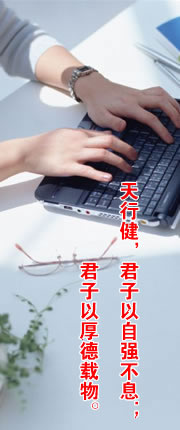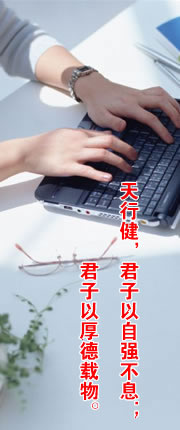|
[案 情]
陈某原系高校毕业生,2001年3月到某展览公司实习,并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约定月收入为1500元,不含提成部分收入。2001年5月1日至6月1日陈某连续一个月未上班,被扣发当月工资并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2001年10月20日陈某再次未上班,展览公司遂于2001年11月1日作出除名决定。2001年12月陈某就劳动关系的解除和提成收入向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2年1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关系,退工日期为2001年10月22日。
2002年8月20日陈某再次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撤消档案中的两份处分决定,赔偿经济损失25000元和精神损失20000元。仲裁委员会裁决不予受理,陈某遂诉至法院。
[审 理]
法院认为展览公司对陈某处理决定,应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告知劳动者。展览公司对陈某处理决定并没有证据表明告之过陈某,又将处分决定塞入陈某档案,客观上必然给陈某就业带来困难。据此,法院判令展览公司撤消处分,赔偿经济损失7130元,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 析]
一、 处分的认定
本案涉及的是两份处分决定,本案的关键也正是这两份处分的有效性。鉴于法院判定撤消两份处分的理由有所不同,笔者在此亦分别加以论述:
1. 关于第一份处分,法院以展览公司不能证明已将处分决定告知劳动者为由裁定撤消,笔者认为不妥,程序上的欠缺不能导致处分实体上的失效。
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企业实行奖惩制度,对职工的处分行为可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问题的复函》对于该条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一般是指: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职工无法履行请假手续情况外,职工不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又不按时上下班,连续旷工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天,即属于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因此,在本案中,如果陈某不能证明其在5月1日至6月1日这段时间内履行请假手续,又无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展览公司是有权对于陈某无故不来上班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分的。
那么,企业的处分必须履行何种程序?程序上的欠缺是否足以导致处分的失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因此,法院认为展览公司按规定应将处分决定告知陈某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证明已经通知的话,笔者认为法院应当责令企业补正其行为,而不是判令撤消处分决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22条规定:用工单位作出对职工的处理决定,虽违反法定程序,但尚不影响处理结论的,可令用工单位自行补正后,维持该处理决定。可见,企业的行政处分与司法审判还是有区别的,司法审判严格强调程序的公正性,譬如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不予质证,提起反诉的案件必须由合议庭审理等等,非经法定程序的判决结果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但是企业的行政管理则不同,只要实体正确,程序上的违法是可以通过补正来维持处分决定,而并不直接导致处分的失效。
2002年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进一步赋予和明确了企业的自主管理权。《解答》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单位处分发生争议的,不涉及劳动合同的解除、变更的,单位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不宜作为劳动争议案件”。企业的处分决定是企业对违纪的劳动者作出的一种惩戒,也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常用的手段。劳动法规定企业有权制定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劳动者,企业也应当有权作出相应处理,人民法院过多的敢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理,不仅限制了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讼累。
2. 关于第二份处分,法院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为2001年10月22日为由,要求展览公司撤消劳动关系解除日后所作出的处分决定。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法院的判令是正确的。
陈某与展览公司一致同意劳动关系的解除日是2001年10月22日,那么在此日期之后双方就不存在身份上的隶属关系,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展览公司对于自己公司以外的劳动者是无权给予任何处分的。但是纵观本案,展览公司作出第二份处分的日期是2001年11月1日,陈某申请仲裁的日期是2001年12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日期是2002年1月,在时间顺序上是作出处分在前,协商解除在后。也就是说展览公司对于陈某的除名已变更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展览公司在同意将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定为2001年10月22日之后,展览公司依然将处分决定放入档案,显然存在过错。
二、 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认定
陈某诉称展览公司的两份处分给予其造成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要求赔偿。法院认为展览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将处分告知陈某,又将处分决定塞入档案,客观上必然给陈某寻找就业工作带来困难,确认存在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则不予支持。笔者认为法院就此认定存在经济损失的理由欠妥。
关于两份处分是否有效已在前文论述,笔者在此假设处分确实错误,那么展览公司是否应当赔偿经济损失?笔者认为陈某诉称展览公司的处分不当影响其就业,侵犯了其就业权,要求展览公司承担的是侵权责任。法律将侵权责任分为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两种。法律对特殊侵权责任的种类是有明确规定的,本案显然不在此例;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的过错、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陈某主张经济损失的不仅要证明处分的违法性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还有义务就其因处分的存在而丧失了就业机会进行举证。法院以处分的存在必然影响其就业为由判令展览公司承担责任有欠妥当。虽然劳动法的宗旨是体现保护劳动者的精神,但是两者的关系如何寻求一个平衡点,如何体现法律对于双方的公平和公正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关于陈某主张的精神损失,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只有三种人格权利受到损害的才能主张精神损害的赔偿。这三种人格权利分别是生命健康权、名誉和荣誉权及人身自由权。本案陈某主张的显然是名誉受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法院不予支持陈某的该项诉请是正确的。
三、 本案时效的认定
我国的劳动争议适用的是60天的时效规定,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起算。在本案中,陈某第一次申请仲裁的日期是2001年12月,达成调解的日期是2002年1月,第二次申请仲裁的日期是2002年8月,因此陈某有义务证明其诉讼请求仍在时效之内。陈某辩称其因屡次应聘未果,遂聘请律师查档,始知处分的存在,并出示了街道盖章的证明。但街道的证明并没有证明陈某何时委托律师查询并得知处分的存在。法院没有就此予以实质性的展开和调查,笔者认为是不妥的。
根据《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等)的档案”。第五款规定:“查阅者不得泄露或擅自向外公布档案内容”。第六款规定:“因工作需要从档案中取证的,须请示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批准后才能复制办理”。职工档案同样是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严格保密的,律师有权调查职工档案的内容,但也要遵行一定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3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定书面委托合同。在本案中,展览公司一再要求陈某举证其何时委托律师查询并得知处分的存在以确定本案是否过了60天的时效。陈某一直未能举证。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对时效未做详细审查武断的认为时效未过是不妥当的。
[ 关闭窗口 ]
|